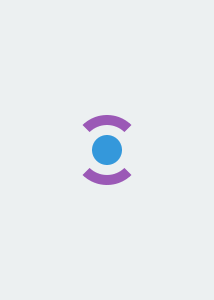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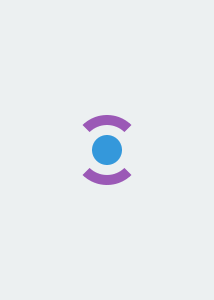
2月18日 凌晨3点18分
江南新村某老式公房内,卧室正笼罩在浓密的黑暗中。床上的男人侧躺着,闭着的眼皮下,眼球快速地从眼眶一侧移动到另一侧,嘴角和手指不时抽搐一下。
刺耳的鸣声响起。正在梦中的瞿省吾被手机铃声惊醒。他闭着眼睛茫然地在黑暗中摸索着床头,伴随香烟和打火机掉落在复合地板上的“噼哩啪啦”声。终于他摸到了闪亮不已的手机。在一天的这个时间他完全无法想起来什么人会在这种时候打手机给自己,却清楚记得昨夜睡觉前忘记关闭手机的不明智行为,他咕哝了一声:“靠!”
他终于接起了电话,清了清嗓子:“你好,平安保险的瞿省吾!”
“救命!救命!”
惊惶绝望的男人的声音如钻头刺进他的耳朵,伴随着急促的喘息声。
瞿省吾突然张开眼睛:“什么?你说什么?”
“嗑嗒”一声,就象来时一样突然,电话挂断了。
那声音无法让他联想到任何熟悉的人。瞿省吾闭上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气,抓搔着自己胡子拉茬的下巴。过了几秒钟,他完全清醒过来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灯看手机上留下的号码--完全陌生。他按了回电的按键,手机中善意的提醒:“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谢谢。”
他回忆着梦境--黑云,沼泽,压在胸口的无形的黑暗,气喘吁吁的奔逃。他用力摇晃脑袋,似乎要把记忆中不连贯的碎片筛除,留下有用的信息。最后他丢下手机,躺下身,拉起被子盖住脑袋,咕哝了一句:“靠!”
24小时 早晨 1
2月18日 凌晨5点45分
普济医院里,星光正在逐渐退去的天空下,草坪上结了一层霜。早班的卫生员拖着扫帚,踏着科技综合楼后花房的砖砌小道慢慢地走着,止不住地打了个哈欠。他闻到一股异味,不由自主地皱起眉头。他用手里的扫帚扫向面前染着污泥的地面。污泥摊开处,腥浓的味道令人做呕。他捏着鼻子弯腰细看了一下,在朦胧的晨光中什么也看不清。
这时一滴冰凉的东西滴在他后颈,摸一把,满手粘稠。他突地打了个寒颤,用扫帚支着地,小心翼翼地扭过头去看头顶。
5秒钟后,临时病房朝花房一侧的病人几乎同时被近乎窒息的嘶叫声惊醒。
2月18日 清晨6点30分
法医病理科的技术员李斌披着白大衣,嘴里叼着装豆奶和包子的塑料袋飞速跑上一层层楼梯。他气喘吁吁地冲进值班法医的休息室,里面床铺已经整理好,但是不见人影。他把塑料袋拿在手里,哼哼着一间间房间去找。空荡荡的实验室里到处是有人存在的迹象--水浴锅换上了新鲜水,昨夜放在电泳槽上连夜进行电泳的凝胶被取下来放在固定剂里固定,窗开着,窗外的梧桐树上传来阵阵麻雀的叽喳。放电脑的隔间里,电脑显示器屏幕黑着,但机箱上的指示灯还亮着,显示处于休眠状态。
“这家伙正值班呢,死到哪里去了?”李斌想着,顺手晃了晃鼠标。黑屏突然亮起,现出欧洲古典建筑的屏幕保护程序,同时喇叭里响起雄浑的交响乐--瓦格纳的“汤豪舍”终场。
“妈呀!”李斌一手捂着耳朵,一手继续晃动鼠标。交响乐响个不停,屏幕上出现一行字母:“please input the protection code:”李斌随手敲打几下键盘,看见屏幕没有反应,推开桌子转身就往隔间外面跑,差点和另一个人撞个满怀。
“这么早就来了?”那人不紧不慢地问。
“你这家伙!”李斌没好气地指着电脑说,“你给我先把这个关掉!我听到这个就头痛。”
值班的人俯身在键盘上敲打几下,音乐声停止,屏幕保护程序关闭,露出WIN98湖蓝色的桌面。
李斌揉着耳朵说:“谢天谢地...”
值班的人问:“怎么这么早就来了?又有尸体吗?”
李斌在装豆奶的塑料袋尖角上咬了一个洞,把塑料袋团在掌心里,象婴儿吮吸乳汁一样吸着豆奶,含糊地应了一声。
“车祸?煤气中毒?还是浮尸?”
李斌苦着脸说:“你等我吃完行不行?我接到电话就赶过来了。据说要尽快检验。科里增派了人手,这次去现场的是金主任自己。尸体很快就要到。说是这么说,不过我看也不一定。”
“哦?为什么?”
“因为得先把死人弄下来,可能要花不少时间。”
“是吗?”
这时办公室里响起了传真机的声音。“案件相关资料已经到了。”李斌匆匆吞下最后一口早点,把塑料袋往字纸蒌里一丢,敞着白大衣往办公室里闪去,象一只白色的动作不协调的大鸟。他整理着不断吐出的传真纸,嚷嚷着说:“哟!照片都来了!现在他们收集资料动作真快呀!”
“哦?是吗?”值班的人跟着进了办公室。经常接触化学试剂而变得粗糙的手指抚平传真纸光滑的边缘。从凌乱的纸堆里,一张工作证复印件被摊平在桌上,年轻男子孩子气地笑着,皮肤白晰,丰润的嘴唇可爱地翘起。下面是姓名和供职部门:季泰雅,医务科。值班的人缓缓地吸了一口气。
****************************
炎热的中午刚刚过去,医学院操场上开裂的水泥地反映着毒日头的白光。一个排球“砰”地拍在地上。男生和女生混合的哄叫声响起:“哦!好球!14比12!”
哨音响起。担任裁判的高年级学生做了一个换发球的手势。参加本场自发组织的男女混合排球赛的药学院队队员按顺时针方向移动。发球位置上站了个1米82的山东大汉,单手转着排球,一副胜局在握的样子。
穿蓝色线裤和湖绿色运动背心的男生正站在左后的位置,烈日的火光刺得他皱着眉头。他望着前面队员汗湿的T恤的后背,悄悄咽下一口唾沫。那人一手在腰间,往背后悄悄摆了个“2”字。
巨掌击出,排球凌空飞过。临床医学院队的前排迅速散开。右后位的队员单手接球,位置偏向左前,他大喊一声:“泰雅!扣球!”刚才偷偷打暗号的人没有往前接球,却往后退出界外。穿背心的男生一个箭步冲上,二传托起了球。两人擦身而过,衣袂相交。人群中有人呼“好球!扣!”话音未落季泰雅便已飞身跳起挥臂扣球。对方立即组起人墙拦网。泰雅跳起后扣球点几乎比他们高一掌,却似乎突然方向不稳,拳缘只是撩了球一下,球往网右方飞去,眼看就要出界。在双方尚未落地时,穿背心的男生却轻松跳起,在排球触网前轻轻一拨,排球“扑”地落在对方界内的真空区。
哨音。“14比13!”
“这球不算!”药学院的女生厉声说,“朱夜擦网了!”
“哪里有!我看得清清楚楚,一点也没有!”临床医学院的女生辩解道。
“输就承认吧!不要不好意思!”
“我们要赢了!你们才死要面子!”
“你什么意思?!”
球技相交很快变成唇枪舌剑。
“真没意思。”朱夜抹了一把汗,“不打了。”泰雅嘟起嘴唇长长地吹气,吹乱自己额前的头发,一手拉动T恤衫的衣领往脸上扇风:“我也不想打了。太热了。”
“上海男人都是软蛋,没品!”对方的男生高叫道,“有种的晚上大操场见!”
泰雅不屑地掠了一下前额的刘海:“你说谁呢!”
“哟,忘了你了!娘娘腔!你也算一个!”说话的男生唱起评弹的音调。对面的男生一起哄笑了起来。
一个女生说:“我们要文明比赛!不要打架!”
药学院的男生说:“上海男人吵上两个小时也不会打。有次我听不下去,冲到人家跟前说两位大哥,你们打吧。你猜怎么着?两个人都跑了!哈哈哈哈!”
“还有还有,粮票还带半两的,抠门抠到锁眼上了。”
“哈哈哈哈...”对方的男生一个劲儿地笑着。
泰雅突然转过身向操场边的树荫下走去。朱夜急忙跟上他:“怎么了?不打了?”
“太热了,不打了。”泰雅操起放在水泥地上的杯子,掀开杯盖,咕嘟咕嘟地喝里面的大麦茶。
对面药学院的男生起哄道:“哦!!!不行喽!挺不住喽!”
泰雅仰头喝着茶,精瘦的脖子上,喉结在小麦色的皮肤下上下滑动。朱夜冷冷地叉着手站着。
药学院的男生觉得没劲,便勾肩搭背地走了,大声嚷嚷着一起去买买冷饮。操场上人群渐渐散了。三三两两的人地走过泰雅和朱夜身边。有人鼓励几句“下次再来”,多数人低头不语。没几分钟,操场的这一角只剩下他们两个。远远的地方,篮球场上还有人在投篮,篮球落地的“砰”声孤独地回荡在空空的操场上。
“去吃冷饮吗?”朱夜问。
泰雅摇摇头。顿了一顿,望着朱夜被烈日晒得褪皮的额头,突然没头没脑地说:“总有一天,我要他们个个仰起头看我。”
********************************************
李斌忙着整理不断从传真机里吐出的传真纸,把它们分门别类裁开理好。
值班的人一手指着季泰雅的工作证复印件,转脸问李斌:“这是嫌疑犯?”
“呵呵,让我瞧瞧...”李斌哗啦哗啦地翻着成叠的传真纸。
值班的人手指不耐烦地划拉着桌面,在那张传真纸的边缘留下道道淡淡的抓痕。
“案情简述,只有一句话,在这里!”李斌得意地举起一张传真纸,“‘普济医院科技综合楼昨夜发生坠楼事件,一青年男子死亡,死者为医务科副科长季泰雅。’呵呵,这个是死者的工作证。哎呀,啧啧,长得这么嫩相,好可怜......搞得这么大,连重案组都出动了,可见是凶杀案。哎,不知摔成什么样子了。但愿不要太碎,否则待会儿收拾起来很麻烦,碎骨头再把管子堵住的话,我们又得挨骂,后勤已经来抱怨了好几次了...”
值班的人手指慢慢收拢,把传真纸捏成一团。他抬头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伸手拉过电话机,拨了外线:“...吴明在家吗?...吴明,是我。你7点半来接班行吗?我有点事情,得早点下班。”
2月8日 晨6点55分
半夜被吵醒后睡得不踏实,瞿省吾早就已经把床铺滚得乱七八糟。现在枕头正在他腹下,床罩翻卷到内面,被里子露在外面,闹钟在床头欢唱“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
他苦着脸爬起来,用力揉了几把发胀的脑袋上杂乱直硬的头发,呆坐了一会儿,突然想起闹钟还在响。他“砰”地一巴掌拍在闹钟背上,拍哑了唱个不停的闹钟。他拖着沉重的步伐进了卫生间,打开电灯,唰地拉开盥洗池上方的壁橱门。他咧着嘴笑了。那些都是帮助他进入工作状态的东西。
厨房电热水瓶自动接通,开始烧水。刮胡刀、须后水、面霜、定型喷发胶、梳子和牙刷排了一排。大约一刻钟以后,走出已经是一个清爽精干的白领青年。他泡了一杯开水,兑上点冷水,吃下几粒维生素和洋参丸,提起拎包出门去。
他下楼走出小区没多远,迈进一家24小时开业的台湾小吃店,点了一碗担仔面加荷包蛋当早饭。店堂里人不少,多数都安静而匆忙地吃着。店堂音响里播放的GDP连续快速增长、股市飘红、外贸顺差之类好消息似乎没有给它增添任何喜庆的气氛。人人保持着开始一天的打拼以前积聚力量的肃穆,如同长途汽车站上等待发车的中巴。
瞿省吾听着各种令群情振奋的新闻,埋头吃着早饭,直到新闻播到最后时,播音员报告了唯一一条坏消息,昨夜318国道上发生连环撞车事故,多辆汽车失火燃烧。清爽精干的白领青年嘴里含着蛋黄,冼练地脱口而出:“靠!”
这几乎是店堂里唯一的声音。
瞿省吾吃完早饭,便加入了痛苦的挤车大军。他还没有加入有车一族,但是他觉得自己每一天都在向这个方向靠拢,前提是他能按质按量完成工作。
他的目的地非常明确。在他分管的这片区域内,普济医院是住院和急诊病人最多的三级甲等医院。在平安保险公司投保医疗险和意外险的患者在普济医院就诊的概率也最大。作为核保员,他的工作是检查这些客户的急诊和住院病史,计算符合理赔条件的款项,汇报给公司,然后客户才能获得保险费。他在普济医院已经是熟门熟路,只要对门口的保安点个头就可以顺利进入。
然而,今天早晨整个医院的气氛明显不同于往日。保安们两两聚着,压低声音谈论着什么,偶尔有人高声怒道:“上面的这些人,老早就该...”便被人拉住袖子,四下望着,重复压低了声音模糊地吐出刚才硬吞下的话。
进门便望见成排的警车,法医的白色面包车,走近草坪,远远只见科技楼和临时病房之间围了一群人。
他拉紧领带,昂首挺胸地从人群边走过,目不斜视。
他在8点05分准时敲开了医务科的门。不能再早,否则医务科的工作人员还在换衣服、交班、泡茶。也不能再晚,否则就有可能被办其他乱七八糟的事情的医药代表、进修医生、研究生、告状的病人家属插在前面,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轮到他。
“早上好!”他带着职业性的愉悦和朝气敲开医务科的门,“季科长在吗?”
满屋子的人突然静下了声,齐刷刷盯着他,空气瞬间凝固。
瞿省吾从来没有在早上的这个时候看到医务科有这么多人。其中很多是生面孔,也有几个他见过,但是以前从来没有在医务科的办公室内出现过。他咽下一口唾沫,暗暗骂了一声“靠!”,随即赔起满面笑容问:“我是平安保险的核保员瞿省吾,要借阅几份我们的客户住院病史,请季科长给开个条子好吗?”
“他不在。”有人生硬地答道。看不清谁在说话。
瞿省吾一边想这帮子人究竟是怎么了,一边搜索着人群,一边以尽量和缓的口气说:“那么庄老师在不在?庄老师也可以帮我开这个条子。”
有人对着阳台说:“彩娥,出来一下,有事情要办。”
人群默默向两边移动,露出一个胖胖的50来岁的办事员。她的眼睛充血,嘴唇因为强作镇定而不争气地哆嗦着,泄露了她竭力想要掩盖地恐惧。她僵着身体半弯下腰,从抽屉里拉出一叠夹在一个大黑铁夹上的“外单位借阅病史证明”,丢在桌上,发出闷重的“哐啷”声,她的身体也为之一颤,泪水从眼眶中满溢而出。她迅速地撩起袖子擦过脸,无声地指了指桌子。
而职业性的笑容已经快要在瞿省吾脸上僵硬。他如获重释地说了声“谢谢”便坐在桌前掏出笔记本飞快地填了起来。填了一两张后他更觉得不自在。没有人恢复交谈。十几双眼睛焦虑的目光充满了整间房间。他知道摆脱这种窘境的最佳方法就是迅速填写完毕,马上离开。他的笔飞速地在纸上唰唰舞动,写下的字连自己也看不清。他把工作证和写好的单子推到庄彩娥面前。她挥手把工作证抹进抽屉里,提起医务科的公章在借阅证明上重重地连敲几下,震得瞿省吾的双脚透过ADIDAS休闲袜和“英国绅士”皮鞋,也能感觉到行政楼这幢老洋房木制地板的摇动。
他最后努力挤出一个更灿烂的笑容,举起手续齐备的借阅单,来不及说声“谢谢”,一头扎向门外。
医务科办公室的门“砰”地在他身后关上了。
24小时 早晨 2
病史档案室在医务科同一幢哥特式洋房的最底里,有长廊通向门急诊大楼和医技楼。这幢房子是普济医院最古老的建筑之一,最初是用做病房,有着宽大温暖的室内阳台,落地窗,长长的走廊在“凹”字形的建筑里四通八达。各种气窗从屋檐的缝隙里透进光线,在古旧的木质地板上投下明暗交错的条纹。在房子造好以后陆续添加的供水、供电、供热、供氧和中央污水管道在墙角、气窗和任何不可思议的空间里盘旋,即使已经废弃很久,仍然和整个医院的复杂管道相通。中央氧气站定时调节压力时从管道中发出低沉的“隆隆”声,仿佛不甘地宣告自己的存在。在“凹”字型的天井里,数十年来逐渐冒出了无数色彩质地不一,高低不齐,功能不同的杂乱建筑,仿佛树根间长出的蘑菇。更奇妙的是,无论建造年代的早晚,都有错综复杂的走道、过道、走廊或楼梯通向行政楼主楼。这些建筑大多本来就粗糙简陋,墙灰剥落,屋角水迹蔓延,有的甚至还带有文革标语和宣传画的痕迹。它们被完全废弃的时间要比老病房晚得多。尽管如此,在几个月后,当科技综合楼的1-5层装修完毕时,行政办公室将全部搬进科技综合楼,所有这些建筑都被一起铲为平地,建造新病房。
他走进病史档案室的时候里面没有人。这里对于他来说更是熟门熟路。他放下提包,翻开包盖,拖出印着“平安保险”瞩目标记的文件夹,摊在桌上最显著的位置,在当中放上印迹未干的外单位借阅病史证明,然后捧着笔记本回头在外间的玻璃橱里找病史。
多数病人出院或死亡后马上就要求理赔。普济医院病史室常把刚出院的病人的病史按照出院的科室和病房一齐放在玻璃橱里,然后每周一次统一按住院号放入病史库。病史室的外间原来是老医院的病房的一部分,用木板隔成两间,病史室的外间是其中一半,另一半属于图书阅览室的一部分。多年来反复修建和改建,使得病史室和图书馆虽然一墙之隔,但要走到隔壁却得走过一条弯曲的走廊。这种情况在行政楼里并非绝无仅有,事实上遍地可见。外间有宽阔的阳台、落地玻璃床,窗沿挂着种在可乐罐子里的吊兰。病史库则把走道封闭形成的宽长空间,没有窗口,连接着深不可测的走廊,仅靠木格玻璃窗上几个通风窗口的小号排风扇排风,散发着消毒药水和霉味的混合味道。而这排风机通向哪里,恐怕只有死后在医院游荡多年的鬼魂才知道。
“毛富根...王常禄...唐来娣...”他念叨着一个个活着出院的投保人的名字,从普外科、泌尿外科和骨科的病史堆里抽出这些病史。“陈仲培...陈仲培...”他的手指翻过一叠叠急诊病人的病史,“陈仲培...”他又翻过一叠叠消化内科病人的病史,最后反复核对笔记本上记录的病人姓名、住院号和死亡日期,确定是普济医院没错。“陈仲培...”他拿笔记本拍着脑袋,在玻璃橱前站着。半开的橱门倒映出通向病史库的幽深走廊。
“靠!上星期日晚上才死,他们怎么会这么卖力...”他倒吸了一口冷气。外间的玻璃橱里没有,那就是说可能已经上了病史库的架子。
那就是说,必须走进那个该死的地方!
他念叨着“陈仲培”的名字和住院号,向走廊深处走去。
病史库的结构象半侧肋排,中间的脊柱相当于主走道,一侧的类肋骨相当于病史架之间的侧走道。在走廊另一侧墙的正上方是一排积满灰尘的木格玻璃窗,陈旧的红漆开裂,掀起,仿若一张张垂死挣扎的病人的嘴。小号排气风扇的叶片在气流的带动下无声地转着。这里储藏着普济医院从作为法国教会红十字医院出现以来130多年来的病史。
瞿省吾念着“陈仲培”的名字,突然想到在这里登录的名字当中,绝大部分已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感到相当不习惯,立刻拉开了病史库里所有的灯和排气风扇开关。嗡嗡的风扇声给他带来一丝人间的气息。
他数着病史架上的数字找过去。最新的病史在走廊底的侧面的架子上,头顶就是一扇嗡嗡作响的风扇。他翻检着叠在一起的病史,默默念着“...陈仲培...”
门外玻璃橱门“呀”地一声,“扑”地碰上了橱框。
他下意识地转头往门外看。走廊明亮的日光灯下,外屋的病史室反而显得虚幻,仿佛是雨季到来前老屋墙上突然变得鲜艳的水粉画。
这时,他感觉有一双眼睛正看这自己。在他转回头来以前,他的眼角看到什么东西在无人的地方掠过。
他抓紧了病史架冰凉的铁框,冷汗从背脊上的毛孔细细渗出。
他慢慢猫下腰,作好向外屋冲刺的准备,一面小心地把头扭向眼角瞥到的地方--头顶的木格窗。
除了嗡嗡作响的排气风扇和积满灰尘的老旧木窗,什么也没有。
他出了一口气,直起身。在未放满的一格上,一份病史慢慢地滑了出来,在滑到架缘时速度越来越快,最后坚决地“啪”地一声落在瞿省吾脚边。他拣起来一看:“...陈仲培...”
他拿着自己需要的病史快步走到外间的病史室,回手拉下病史室的灯和风扇开关,关上门,深呼吸,然后开始工作。
他还没翻几页,病史室的职员鲁巧音捧着一大杯热茶踏进了房门。
“鲁老师,早!”瞿省吾招呼道。
鲁巧音点头作答。她的脸色有点苍白,似乎超过了廉价粉饼的功效。
“今天天气不错呐!”瞿省吾乐呵呵地说,“马路上没什么积水。”
“哎...是呀。”
“怎么没见着季科长呢?又出差了么?”
她的嘴唇霎时颤抖起来:“呀!你还没听说么?”
“听说什么?谁都没对我说什么呀?”
鲁巧音搓着手里的杯子,连打了几个寒颤:“季泰雅...死了。”
“什么?怎么可能!”瞿省吾真正大吃一惊,“为什么会死?怎么死的?什么时候?”
面对他下意识的连串问题,鲁巧音只是摇头:“现在什么都不知道。公安局的人来了,不少人。和领导谈到现在。谁都不知道谈了什么。好端端的一个人就这么死了……撞了鬼了……”
突然,单调的鸣声直刺耳膜。瞿省吾匆匆掏出手机,点了一下头,冲出房门来到走廊里。他沿着宽大的楼梯下到拐角的窗前才接通电话。在这里工作一阵子以后他发现这里是信号最好的地方。
“瞿省吾,你现在到普济了吗?”电话那头是理赔经理高天的声音。
“是,我到了。”
“那几个理赔的事情先放一下,有重要任务。”
“哦,什么任务?”
“普济医院有个投保人今天身故了,马上要进入核保程序。”
“受益人申请理赔了么?”
“没有。记住他的名字,你应该认识...”
“季泰雅?”
“你已经知道了?”
“我大概是全院最后一个知道的。这儿到处是警察。是警方要求调查的么?”
“还没有。听着,这个人投了好几种险,有医院给保的,也有自己买的,数量非常大,光是‘99返本人寿’就买了20多份。真他妈的有毛病!这人早就进入我们的特别监察范围。我刚才粗粗算了一下,合计身故保费100多万。”
瞿省吾好不容易压下快要奔逸而出的“靠”字,咳嗽了几声:“超过5万的理赔,要进入301程序了吧?”
“对,就按301的原则办。别忘了,我们这个季度的理赔额度已经超了,现在才什么时候!我们不是开印钞场的,不能把公司的钱流水一样赔出去。这家伙已经有投资连结、附加医疗和意外险,几十份寿险和一种短期意外险,过年前又刚买了5份含大额身故保障的寿险,要注意有没有骗保!千万注意!你现在在哪里?”
“在档案室。”
“有传真机吗?”
“等下我问一声……”他冲回档案室问:“有传真机吗?”
鲁巧音正捧着茶杯坐着发呆,被他一问,吓得在座位上跳了一下。待她回过神来,还是哽住了喉咙说不出话,指了指屋角桌子上的传真机。瞿省吾一边说谢谢,一边用空着的一只手在抽屉里翻找,终于找到了登记本上传真机的号码,报给经理。
“好的。基本信息我会尽快用传真发给你。你等着。”
“我明白!”
301是个不成文的规定的俗称。凡是有高度骗保可疑的身故事件,必需向调查的警方正式提供信息,主动配合调查。
他收了线,对鲁巧音说:“我能用一下传真机么?”
她有点茫然地点了点头。
“这些病史能不能先放一会儿?那些警察在哪里?我找他们有事。”
她用同样的动作点了点头:“在二楼那一头的小会议室里。”
24小时 上午 1
2月18日 晨7点50分
方文涛院长一手拎着白大衣,一边匆匆地穿,一边匆匆地走,脚步快得身后的人得迈开大步才能跟上。从医技楼通向行政楼的水磨地走廊里,一片急促的脚步声。
院长不停地发问,精干的院办秘书在喘息间期不停地回答。
“什么时候发现的?”
“早上6点不到。”
“确实是他么?”
“法医做了现场检查,血型相同。”
“谁最早到现场?”
“内科总值班,内分泌科的金洁。”
“现在扩大到什么范围?”
“围观病人和家属很多,我们已经联系保卫科,尽一切可能保护现场,配合警方调查。”
“有没有影响病人情绪?”
“现在应该还没有。医院秩序正常。”
“刑警什么时候到的医院?”
“7点不到就到了。还来了几个法医。尸体马上要运走解剖,不放我们医院的太平间。”
“不放我们医院的太平间?你们想想,为什么?”
在两条走廊相交的空地上,院长突然停下脚步,身后追随的院办秘书、党委书记、医务科科长郑怀德和保卫科科长差点撞在他身上。一行人喘着气。院长盯着下属,下属盯着地板,各人心里涌动着一大堆话,却没有人首先开口。
院长向四面望了一下。远远的走廊那头通向医技楼B超室的地方有几个早来排队等候检查的病人在向空荡荡的走廊里张望。看见聚起的这几个人,很快一晃而过,在门那边消失了。
院长压低而深切的声音狠狠地一字字吐出:“我们医院130年没发生过谋杀!”他扫视着眼前的这些干部,重复了一句:“130年!”
保卫科科长慢吞吞地开口说:“这件事情,警察还没有下结论。”
“结论?”院长利剑般的目光直扫医务科科长郑怀德,“结论,你们心里自然有底。”
郑怀德的额头早已沁出汗水,此时他顾不上擦汗,急急地说:“季泰雅确实正在接受经济调查,但是,调查的强度并没有超过一般的限度。在这几天以前他精神压力很大,我和他谈过几次,虽然他没有直接说起过有寻短见的念头,不过现在的年轻人心高气傲经不起挫折的多的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会有什么反应,我们确实很难预料。”
党委书记补充道:“现在社会上乱得很,半夜有坏人从外面进来也有可能。”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保卫科科长正要辩驳,被院长的目光逼了回去。
院长压低声音说:“别再说这些了!警察正在等我们。先把他们对付过去再说。”
一行人保持着原来的速度向小会议室走去。在小会议室门前,院长突然立定。他握住小会议室的门把手,沉吟几秒钟,用力拧开门把手推开门。他的下属跟在后面鱼贯而入。
小会议室正在晨光中逐渐明亮起来。几个穿制服的人的剪影印在窗前。其中一个转过头来说:“方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