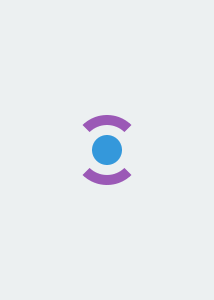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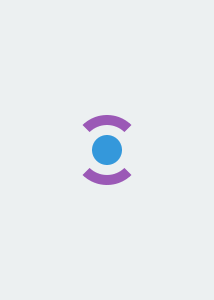
表现主义土壤中的另类之花
影片虽然改编自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但其本身却富有表现主义色彩。20世纪二三十年代正是欧洲先锋派电影如火如荼之际,而德国表现主义电影是欧洲先锋派运动重要的组成部分。德国表现主义受印象主义影响,先后在绘画、文学、音乐、戏剧等艺术领域发展成为一场文艺运动,德国电影浸淫在这样的氛围中成为较晚被表现主义支配的艺术形式,持续时间也不长,但却精品迭出,影响深远。
第一,主观真实的展现。表现主义电影常常追求内心世界的外化,通过变形和夸张的处理,将现实世界转化为内心自我的折射。主人公失掉职位,实在留恋那套让他自豪的制服,悄悄返回酒店偷走制服。当他抱着制服狂奔逃出酒店,已是身心俱疲,回头望去,眼前的大厦慢慢倒向自己,几乎压在身上。这组蒙太奇将看门人担惊受怕,已无法掌控局面的失衡心态展现得淋漓尽致。而后回家喝醉昏昏欲睡,梦见自己仍为看门人,而且力大无穷,能将重箱子单手举起,杂耍般在顾客面前表演,引来阵阵喝彩,导演用幻构的影像修辞方式将主人公留恋这份工作,不愿脱掉制服的心态夸张地呈现出来。
第二,夸张的表演风格。表现主义电影的表演常常抽掉对个别细节的展现,不塑造立体可信的角色,而是强调象征性、抽象性,以极端替代典型。强宁斯在本片的表演虽说比“卡里加利博士”收敛许多,却依然保持夸大和戏剧化的特征,萨杜尔甚至固执地认为“强宁斯没有表情的面孔和夸张、生硬的演戏姿势毁坏了《最卑贱的人》”。此外,在灯光方面,放大的人影、黑暗的洗手间入口均能体现出表现主义影片用光特点。
作为室内剧的《最卑贱的人》却表现出了与表现主义电影相异的另一鲜明艺术风格和旨趣——现实主义。在影像上,首先表现为人物生存环境的全方位展示。影片放映了两个阶层完全不同的两种生活,一个是穷人,生活在底层处境艰难;一个是富人高高在上,养尊处优。看门人成为将两种生活融合的中间人,穿上制服便可以出入高档酒店,而下班后则回到贫民区,那套制服因此显示出神奇魔力。通过看门人的活动,将高档酒店与城市贫民区生活并置,从而使上流社会的穷奢极欲与下层市民的穷困寒酸形成了鲜明对比。其次,在人物设置上,突出表现小人物的生活和心理。不再以疯人、怪人、残暴统治者为描写对象,把镜头转向普通人像工人、职员、仆人等是这一时期“室内剧电影”的一个特征,然而“这种直接以小人物为主人公,以毫不犹豫的批判为主旋律的创作在当时的德国电影里是较为少见的”。
影片不仅成功塑造了一位老守门形象,也将失去原来“荣耀”工作后的失落,不得不从事“卑贱”工作的无奈,最后又飞黄腾达的傲慢心态成功再现。再次,现实主义电影表现手法的运用。影片长镜头运用十分广泛,如守门人清晨上班时遇到玩游戏的小孩,当上下楼时,对邻居们的展示都具有极强现实感。影片甚至用一个固定长镜头表现了看门人从下班回家,天色变暗,经过黑夜,天色又逐渐变亮的过程。以《最卑贱的人》为代表的室内剧电影是德国现实主义电影发展链条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虽然孕育在表现主义的土壤之中,《最卑贱的人》却有着现实主义的“筋骨”,这也使其成为德国电影史上的一朵奇葩。
影视语言的推陈出新
在《最卑贱的人》中,导演茂瑙运用了当时最为先进的影视拍摄技术,丰富了影视语言的表现力,在当时的欧洲,甚至美国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对电影史发展贡献最大的德国电影之一”。克拉考尔在谈及此片时说道:“由于摄影机实现了的高度灵活性,《最卑贱的人》强有力地影响了好莱坞运动画面的技巧。”
影片在影视语言上的开拓最主要体现在移动摄影技术的运用。移动摄影并不是茂瑙等人的创造,它几乎与电影同龄,在1896年法国摄影师普洛米奥拍摄影片《威尼斯风光》时,就运用了移动摄影方式。后来,摄影师在汽车、火车、飞机甚至架空索道上拍摄,以获得移动镜头。茂瑙和摄影师卡尔·弗洛恩德在拍摄过程中,利用梯子、自行车、摄影车,甚至把摄影机绑在演员身上的方式,将摄影机从固定三脚架中解放出来,把移动摄影“升格成为一种完全流动的视觉叙述技术”。
第一,移动摄影引起丰富的视点变化,使观众积极介入叙事情境。运动镜头在叙事中具有更多的主动性,引领着观众的注意力跟随被拍摄对象不断移动,使观众的视线、人物的视线和镜头的视点“重合”,让观众产生身临其境之感,使影片更加生动逼真。在影片中,看门人酒醉后做起“白日梦”:自己变得力大无穷,单手举起巨大行李箱,在众多顾客面前炫耀。镜头从看门人走进转门开始跟拍,进入大厅后,晃动的镜头扫过顾客惊奇的面孔,再拉回到看门人高高抛弃起行李箱,然后再次环摇顾客为其喝彩。这个移动长镜头将观众带进主人公的梦幻中,镜头关注顾客的表情,视点与看门人视线重合,因为他渴望得到顾客的认可,想让别人承认自己还有能力胜任这项工作,而晃动的镜头、模糊的画面则提醒我们这不过是主人公的黄粱一梦。
第二,移动摄影创造了长镜头,使影片不仅具有现实主义风格,产生丰富的意蕴,还有效控制了影片的节奏,既流畅自然,又简约精到。看门人穿偷来的制服回到家中,此时邻居已得知其丢掉原工作,便悄悄躲在门后看他出丑,摄影机不断跟随主人公向后拉,前景是战战兢兢羞愧难当的看门人,后景是邻居次第从门窗中探出头来对其哂笑,层次分明,而内蕴丰富。影片结尾,导演用一个流畅的移动长镜头介绍了重新出场的主人公,可谓层层铺垫,浓墨重彩:镜头向后依次拉过酒店大厅内多个用餐的顾客,他们为报纸上的新闻开怀大笑,最后镜头一摇,在另一个餐桌上,多名侍者正在为一位贵宾服务,侍者闪开,镜头推上,是一个巨大蛋糕,蛋糕移开,正是报纸新闻的主角,原来的看门人,成为了如今的百万富翁。
另外,独特的剪辑方式产生出内蕴丰富的修辞,为影片增色不少。例如,当看门人得知经理调换了工作,难以抑制心中的愤懑,试图将面前的一个大行李箱举起,结果摔倒在地,直接接入一个年轻看门人风雨中矫健地扛起行李箱的镜头,这既可以看做是导演有意设计的对比蒙太奇,也可以看做是导演使用幻构表现他的心理现实。反复出现的转门,成为“一种心魔”,成为命运轮回转变的象征。
“理想的电影不需要字幕!”这是茂瑙在拍完此片后如是说。电影语言演进到此,终于可以抛开字幕而独立叙事了。
关于结尾
影片有一个“光明的尾巴”:看门人意外获得巨额遗产,由“最卑贱的人”变成最幸福的人,从地狱升入天堂。关于结尾评论界向来褒贬不一。有人认为,削弱了其现实主义批判力度,画蛇而添足;有人认为,增强了其讽刺效果,是画龙点睛之笔;有人认为,“表示了对这种基于偶然和运气的幸福结局的怀疑”。
电影具有梦幻特质。人们走进电影院,把现实生活中受到的压抑情绪、愿望和无法实现的理想投射到银幕中,通过剧中人物命运变化得以实现,从而使自己心理满足,情感得以宣泄,心态获得平衡。好莱坞经典影片深谙此道,将电影的梦幻性发挥到了极致,制作出许多经典喜剧剧情片。或许本片创作者对主人公的遭遇充满同情和怜悯之心,笔者却认为,茂瑙和梅育的大团圆结局是对好莱坞叙事方式的认同和接纳,是对强大的美国商业意识形态的臣服。通过《最卑贱的人》和《浮士德》两部电影,茂瑙和梅育向世界,尤其是好莱坞,展示了运用影视语言的娴熟技巧和对好莱坞叙事规则的认同,并为其赢得了进军好莱坞的敲门砖。
本片拍摄于20世纪20年代。那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人们的精神处于混乱、狂暴、无所顾忌之中,欧洲电影也开始了新一次的崛起。法国、德国、苏联的电影艺术家们开始了一轮无拘无束的对纯电影的追求,即“欧洲先锋派电影运动”。战争击碎了旧有的顽固条例,一切有待重建,电影的追求者们开始根据自己对影像艺术的理解推动电影车轮的前进。法国印象派注重心理描写,极力渲染个体情绪;超现实主义各流派对纯特技的追求,以及跳出理性回归混沌真实的头脑风暴。苏联开始了电影蒙太奇的试验。而德国表现主义由浓墨重彩地渲染最终走上了现实主义的道路。在由表现主义向现实主义过渡中,室内剧和街头电影做出了极大贡献。而本片即是德国室内剧中的杰作。
表现主义通过极具象征意味的舞台布景、光怪陆离的灯光音效,塑造了一个超现实的只存在于角色脑中的扭曲的幻觉世界。这种将角色情感思维的外化带有试验意味,推动了电影的发展。在此之后,严谨的德国人开始探索表现主义电影中蕴藏的社会性。发展了以小人物为主角的追求真实的室内剧。
本片的故事情节极简单,可以将之概括成“小人物的悲哀”,这也是当时德国室内剧、街头剧的表现主题。一个来自贫民区的老人以当大酒店的门房为自豪,随着年龄的增大失去了力气,被经理贬去当上了厕所侍者。接着临到他的便是自我的绝望、他人的轻贱嘲讽,以及为虚荣偷制服后的负疚和惶恐。但悲哀旋涡的终结很出人意料,老人意外获得了大比财富。接着便以自己的观念对社会阶级进行了新的评判。
《最卑贱的人》虽然在涉及到小人物的生活情感这一层面上是难能可贵的,但一切都过于夸张,有木偶戏的感觉。但这也就是无声电影的表现方式,似乎是无可厚非的,只是作为现代人的我不大适应罢了。
片名“最卑贱的人”起的很精确。编剧导演似乎想告诉我们:小人物是不卑贱的,只要他认清自己,勤恳劳作。卑贱的是像老人一样不敢面对自己的真实地位,追求虚伪的荣耀,甘愿为富人鞋底的泥土,还为此沾沾自喜的人。除此之外,导演还想表达的是当时社会贫富急遽分化,阶级观念深入人心,甚至取代了人个人性成为评判人物的标准(老人的一身制服比他这个人更能换得尊敬)。再次,即使在同一阶级中也是没有温情的,位高则奉承,位低则鄙视,甚至自己的亲侄女也不愿与没有了制服的老人相认。
本片是根据果戈里的小手《外套》改编的。果戈里作为同情小人物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倾向于将人物归类,以类判人,这正好契合了德国室内剧的表现方法:作品集中在“寓言似的人物”身上,去批判一切人,以及所折射出来的社会现实。在进行归类的时候就相应地失掉了人物的丰满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