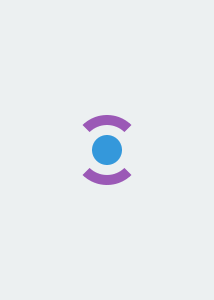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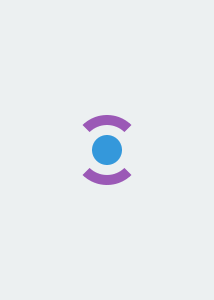
今年共有七部长片和六部短片将角逐2017年酷儿棕榈奖,目前口碑爆棚的《每分钟120击》,在此竞赛单元处于领先地位。
与同样讲述艾滋抗争的美国电影《平常心》不同,《每分钟120击》并没有平铺直叙地表达政治诉求,而是通过群像清晰地展现出90年代法国艾滋以及性少数群体的真实境况。
《每分钟120击》讲述了上世纪90年代,艾滋风暴席卷资本主义世界。年轻人不满制药公司垄断科研成果,他们组建了激进组织Act Up,轰轰烈烈的走上街头对抗社会冷漠。两个年轻同志一起投身抗艾事业,最终却因为理念冲突而分道扬镳。
在这部影片中,男主角Sean是个艾滋病毒携带者,即便身患不治之症,但Sean却丝毫没有表现出对死亡的担忧,他忙于在社群中出谋划策,积极冲向抗争活动的第一线,面对恐同人群他更是敢于大胆亲吻同伴回应对方的挑衅,并因此收获了一段爱情。
然而,爱情并不能阻止艾滋病魔的侵袭,死亡就像幽灵一样等待随时降临。但是,虽然斗士Sean走了,他所追寻的目标还在,他的灵魂还在追寻。
罗宾·坎皮略
本片由法国著名编剧罗宾·坎皮略执导,他的编剧作品《课室风云》获得了第61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他执导的处女作《东方男孩》(Eastern Boys)获得了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大奖。
在戛纳电影节的新闻发布会上,导演罗宾·坎皮略就创作动机、对巴黎激进组织Act Up的理解以及电影所反映的关于艾滋病真实痛苦的刻画等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巴黎Act Up组织对你意味着什么?
坎皮略:我1992年4月加入该组织,也就是艾滋病爆发的10来年后。作为一名男同性恋者,整个80年代我都是在恐惧中度过的。
在90年代早期,我在电视上看到了该组织创立者之一Didier Lestrade的采访,他谈到了一个已经建成的“艾滋病社区”,在那里住着饱受艾滋病折磨的人,病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以及抗击艾滋病的医护人员。在当时整个社会都缺乏关注的情况下,这些医护人员得到的支持是最少的。他的采访打破了长达十多年的沉默,也就是在那时,我决定加入巴黎Act Up。
我第一次参加该组织的会议,就被它散发出来的活力所震撼,考虑到当时我们处在艾滋病最肆掠的时期,人们这样自由地谈论艾滋病是相当难得的。在80年代感染上艾滋病而身陷绝望的男同性恋者们,公开集中地成为了抗击艾滋病的主要斗士。
他们积极影响着身边的人,向大众普及艾滋病相关知识,教他们艾滋病医学表述上的技术特点以及争取集体权利斗争中的政治阐述。
但是,归根到底,Act Up是由一个个拥有坚强个性的个体组成,换成别的环境,他们似乎没有什么理由能聚合在一起。抗击艾滋病运动的力量很有可能来自这群试着求同存异、达成共同诉求的人之间碰撞出来的巨大火花。
我虽然在组织中只是个普通成员,但我相当活跃。我加入了医疗委员会,参加了许多次的行动,这其中的一些行动给这部电影带了灵感。在那个时候,需要明白的是,在高中谈论安全套以及问毒品使用者交换针头都是不合乎标准的。那时,恐同才是标准。确实,我们忘记了从那时到现在社会是怎么演化的。关于事物以前是什么样的,人们似乎趋向于选择集体失忆。
电影中多次出现的会议场景
你是怎么定义这部电影的,是重构还是自传呢?
坎皮略:这部电影当然是虚构的,就算我试图在电影中重建当时发生的许多次大讨论以及开展的行动,我都是很自如地把它们嵌入在叙事里面,而不是生硬突兀地如实反映它们本来的面目。
我非常希望年轻人能直面这个故事,同时,与年轻的演员合作也让我完全避免了去模仿真实人物的冲动,尽管我认为把当时讨论的强度以及人物声音的音乐性带入电影是十分重要的。一旦我找到了那个平衡,人物的个性就突破了模仿的限制,从而自然而然不加拘束地散发出来。
那么,对公开会议的展现,让你将政治叙述转化成一部电影的主题?
坎皮略:对公开会议的展现是这部电影的主要方面之一,同时也超越了会议本身。Act Up组织的中心策略是在对抗中去具体展现艾滋病这个疾病,也就是被艾滋病摧残的满目疮痍的躯体。
在针对医药公司Melton-Pharm的行动中,Sean对医药公司的总监说,“这就是艾滋病人的样子,要是你们从没看过拖着疾病的躯体的话,你眼前的就是。”艾滋病人总是被忽视,人们似乎看不见,但通过有血有肉的体现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政治主题。在这部电影里,体现既是一种政治态度,也是一种电影选择。
电影主创人员亮相本届戛纳电影节
电影的最后执行了安乐死,你认为Sean是死于艾滋病吗?
坎皮略:电影对Sean的艾滋病发展阶段留下了一个开放式的问题。一般来说,Sean的情况应该是随着电影的进程而不断恶化的。但是,我认为重要的是去展现他在隧道里的一切:一切都再也回不去了,当与外面的世界相连时,这就达到了脆弱的极点。
对Sean来说,问题就是承受这一切,等待生命结束。在艾滋病爆发的时期有许多秘密进行的安乐死,也许现在人们才开口说罢了。
“每分钟跳动”意味着音乐节拍或是心脏跳动,就从电影的名字来讲,你似乎更多在强调音乐的作用?
坎皮略:老实说,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浩室音乐,也并不是每次行动结束后所有人都去夜场寻欢作乐。但这种音乐吸引能让我及时地触及一个具体的瞬间。
我不禁会想,这音乐,不管是欢快的还是不祥的,都可以作为这段时期的背景音乐。因此,在我看来,这音乐更能让人联想到艾滋病爆发时初期的日子。
今天来说,拍这样一部电影有紧迫性吗?
坎皮略:在这个特别的时刻,选择拍这部电影而不是其他的片子,在我看来,显然是有原因的,因为我需要这样做。我想要讲述这个故事,因为我觉得还没有人讲过这个故事,比起怀旧,它需要被更广泛地传播。
我不认为电影能对政治造成直接的影响,也不是诉诸于一些现在已经不起作用的解药。在我看来,这与怀旧无关,因为不可能想象我们会忘记那些年的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