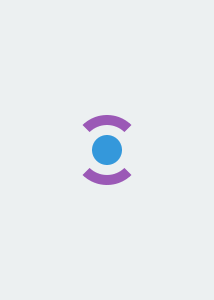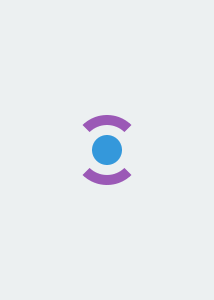《泄密的心》中文译名为什么是《泄密的心》?
the tell-tale heart译文如下:
《泄密的心》描述的是一个神经过敏、精神变态的年轻人,因为邻居老头有一只像兀鹰的眼睛而对老头产生一种病态的仇恨,这种仇恨越积越深,于是他产生了杀机。终于,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年轻人杀死了老头,并肢解了尸体,将支离破碎的尸体全部塞入地板中间。在整个过程中,年轻人自认为谨慎巧妙、天衣无缝。
当警察前来盘问时,年轻人表现得镇定自若,甚至大胆地搬来椅子,坐在隐藏老头尸体的地方上,和警察们聊了起来,可是不久之后,年轻人仿佛听到了老头心跳的声音,这种声音越来越响,最后,年轻人精神濒于崩溃,招认了杀害老人的事实。
该短篇小说中交织着疯狂与理智,时而理智,时而疯狂,理智中带有疯狂,疯狂的行径下又透露着隐藏的理智,而这样的情形没能回答“我”从始至终提出的问题:“你认为我疯了吗?”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也导致了“我”对这个问题佐证与询问的无意义。
同时,这种疯狂与理智的相悖,也使“我”并没有获得杀害老人这件事的预期意义。因为老人眼睛给“我”带来了不安全感,为了逃离被透视的冰冷的感觉,“我”杀死了老人。但老人的死没有带走不安全感,越来越快的心跳声昭示着越来越严重的不安全感,“我”也淹没在这心跳声中,最终暴露在警察面前。虽说“我”到底有没有疯这个问题没能得到解决,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即是否定了“我”没疯,这个“我”期望的回答也证实了单用“疯了”来形容“我”并不全面,也证实了“我”的不安全感没法通过杀害老人得以驱除,老人不是“我”真正害怕的。
英语短篇小说泄密的心翻译
泄密的心
爱伦?坡
真的!焦虑,很焦虑,极其焦虑,经久以来,我都超级焦虑;可是为何说我疯了?病痛消弱了我的知觉——木有消除——木有麻痹我的知觉。先说说我的听力。放耳听去,天上人间,冥界繁事,尽收耳内。所以我怎么算是疯子?听仔细了!我可以不紧不慢、心平气和地告诉你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
讲不清啥时候第一次冒出这念头;但自从想过后,它就日日夜夜萦绕心头。木啥目的,也木啥贪念。我还挺喜欢那老人。他自从木有烦扰,甚至辱骂过我。我也不念叨他的小金库。我想:是他的眼!对,就是他的眼!他其中一只眼像秃鹰眼一样——苍蓝色。每次他看我,我都全身凉透了;所以,自然而然,我决定灭了他,永远脱离出那阴冷的视线。
此时正是关键。你当我是疯子?疯子可是什么都不知道。你已经明白我做事多么理智,多么谨慎,多么高瞻远瞩——我若无其事地上班!杀他前一星期,我对这老人超殷勤。每晚,午夜,我打开他的卧室门——哎,要多轻柔就多轻柔的说!接着,门缝够容下脑袋时,我就伸进去一盏提灯。灯被裹得紧紧的,黑乎乎的,一丝光都不透的。然后我伸进头。哈哈,你要是真看到我怎么机智地进去的,你肯定会点32个赞的!我慢慢的,很慢很慢,超级缓慢地伸进头,当然吵不醒那熟睡的老人啦。差不多1小时后,我才完全伸进头去,就看到他躺在床上。哈哈——疯子有这智商?后来,我可以方便点动时,就打开提灯。哇塞,我那么谨慎,那么小心,刚好露出一丝光线,正好投射到他那秃鹰眼。
连续七晚,我都干这事——每晚午夜——但是他眼睛一直闭着的;我没办法下手;因为惹火我的不是这个老人,而是他的魔眼。每天早晨,我进屋,亲切地和他交谈,夸奖他,呼唤他,问候他睡得好吗。因此正如你所见,实际上他是纯良之人,毫不怀疑每晚午夜时分我窥视他的睡颜。
第八天晚上,一如既往,我极其小心地开门。动作比手表分针还磨蹭。此前,我从不知道我预见能力这么厉害。胜利在望,我又害怕又激动。心有所思地一点点推开门。他做梦都想不到我的心思我的行为。一想到这,我咯咯地笑了。莫非他听到了?他好像惊醒,突然动了。你可能猜我现在会退缩——错。他房间那么黑,暗黑得不得了,(他害怕匪徒所以紧绷着身子颤抖。)因此我知道他看不见门在打开。我依旧偷偷摸摸地推开门。我伸进头,要开提灯,手指刚滑过灯线,老人在床上跳起大吼“谁在那?”
我一动不动,始终沉默。一个小时过去了,我一丝肌肉也不曾松懈。这时我听到他躺下的声音。他也躺在床上听着——如同我夜夜做的那样,听到死神注视着墙面。马上我就听到极低的呜声,我晓得这是神经恐惧才有的声音。这不是因为疼痛或忧伤而产生——绝不是!这是过度惊悚时,从心灵深处升起的阴郁的颤抖的声音。我深知这声音。每每深夜,万物皆眠,唯我梦醒子时,内心深处、灵魂深渊中就发出这种声音,回声阵阵,让我恐惧到崩溃。我说了我了解这种声音。我知道老人想啥子。虽然我心里窃笑但我仍可怜他。我知道从第一次轻微声音使他在床上转身时,他就一直清醒着。他越来越害怕。他尝试去忽视,但这不可能做到。他不停地自语——“什么事都没有,只是烟囱里的风——只是老鼠穿过地板”或“只是蟋蟀的声音”。是的,他一直这么安慰他自己:但是白费力气。毫无作用;因为死神来了,都站在他面前和他的影子谈判,签约受害者了。老人感觉得到阴郁地黑影——虽然看不见听不到——却真切感知我存在在房间里。
我耐心地呆了很久,还没听到他躺下的声音。我打开了提灯,仅露出一丝缝隙。我开灯了——你想不到我有多偷偷摸摸地开灯——终于,从蜘蛛丝般细的狭缝里射出一线光,落进那秃鹰般的眼眸中。
睁着眼睛的——挣得大大的——看到这些我变得激动。我清楚明白地看到它——苍蓝的眸,似蒙了昏沉的纱,让我感到彻骨寒气;但我看不到老人的脸或身体:因为我顺着光线直接精准锁定目标。
跟你说了没?有这么敏锐的感官会是疯子?——此刻,我听到一种声音,沉闷,模糊,像是钟表在棉花里发出的声音。我也熟悉这种声音。这是老人的心跳声。我更为兴奋,好像受到鼓声激励的士兵。但是我依然克制自己,保持沉默,呼吸都有些胆怯。我恍惚地提着灯,小心地保持光线照在那眼上。同时,那该死的心脏跳得更欢了。速度越来越快,声音越来越大。他一定怕极了!声音越来越大,分分钟变大!——你懂我意思吗?我说过我焦虑:我现在就焦虑着。今晚,挺尸的时,房内死一般的沉寂,多么搞怪,我惊讶有这声响竟让我产生难以抑制的恐慌。目前为止,我仍极度克制,数分钟一动不动。此时,我异常焦虑——邻居会听到声音的!动手时候到了!大吼一声,扔掉还亮着的提灯,我冲进房间。老人惊叫一声——仅一声。我一下把他抓到地上,掀倒厚重的床板压住他。然后我会心地笑了。可是,过了很久,他心脏还跳着,发出那种沉闷的声音。不过这回我没发火;隔墙听不到这声音。终于声音消失了,老人死了。我移开床,检查尸身。的确,他死得硬硬的。我手在他心脏那很久,没有感觉到脉搏。他最终死了。他的眼再也不会烦我了。
还当我疯了么?听完我多么聪明细心地藏尸后,你就不会这么想了。夜深,我安静地忙碌着。首先,肢解尸体,砍下头、胳膊和腿。接着拿起卧室地板上的三个木板,把尸块放入方格。然后重新放好木板。我如此聪慧如此机敏。没人,就算是老人的眼——也察觉不到异常。没啥要清洗的——没任何污渍——没血斑,啥子也没有。我超级谨慎地处理了。都用澡盆清洗过了——哈哈!
都处理完,到四点了——天依然漆黑如午夜。钟声响起,街上传来阵阵敲门声。我淡定地下楼开门——我还有啥怕头?进来三个人,他们和善地介绍自己是警署人员。那晚邻居听到那声尖叫了;已经怀疑涉嫌谋杀;他们在警局登记了信息,已经开始着手调查。
我笑了——我还怕什么?我欢迎他们进屋。我说,我做梦时尖叫了。还说,老人去乡下了没在这。我让调查人员在屋子里全部查看下。我请求他们好好查查——查仔细了。我带他们去他的卧室。我给他们看他的财宝,一分不少,稳稳当当地放着呢。我相信自己,所以我热情地搬了椅子进那间屋,招呼他们坐,缓缓疲乏。而我自己,肆无忌惮,坐在存放遇害者尸体的位置上的那把椅子上。警察们很满意。我的举止取信了他们。我非常放松。他们说话,我也开心地回应着。他们聊着类似的事情。不过,一会儿,我觉得不舒服了,我想他们先离开。我头疼,幻听到铃声:但他们还坐那儿聊天。铃声清晰了,越来越清晰。我说得更加流畅,不顾自己的感受。可是声音还在,更清晰,更悠长,原来不是在耳朵里响的。
毫无疑问,我现在很虚弱——但是我说得更流利,声音高昂。声音越来越大——我能怎么办?有低沉的模糊的频率很快的声音——像棉花里的钟表声。我呼吸不顺——警察还没听到吧。我说得更快速——更激动;可是杂声自动变大了。我提高嗓门,嘲讽争辩,声音高昂,举止粗鲁;但是那声音还在增大。他们为什么还不离开?我大步走来走去,好像被人们看着而激动起来——但是他们干吗还不滚?我要怎么办?我吐口水——胡言乱语——发誓!那些人正愉快地谈笑。他们可能听不到?万能的神呐!——不,不可能!——他们怀疑啦!——他们嘲笑我的恐惧!——我止不住地这么想。但是没什么比这痛苦更糟糕了!没什么比嘲笑更不能容忍的了!我受不了这些虚伪的笑容了!我感觉我要么咆哮要么去死!——此刻——又来了!——听!吵!很吵!更吵了!越来越吵!
“够啦”我吼叫“别装了!我承认我干的!掀开地板——这儿,就这儿——就他的心跳声在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