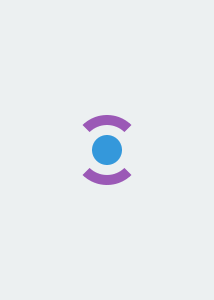伍子胥是否掘墓鞭尸,从历史记载中分析
根据《史记·伍子胥列传》记载:始伍员与申包胥为交,员之亡也,谓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吴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申包胥亡于山中,使人谓子胥曰:“子之报仇,其以甚乎!吾闻之,人众者胜天,天定亦能破人。今子故平王之臣,亲北面而事之,今至于僇死人,此岂其无天道之极乎!”从这里来看,伍子胥鞭尸却又其实,但是我们不能单一的从这一方面来看。
伍子胥究竟有没有掘墓鞭尸呢?我们来看看一位学者的详细分析。
伍子胥在父兄被戮后,智过昭关,投奔吴国,导吴破郢,掘楚平王之墓,鞭尸三百,终泄心中积恨,是一段载诸史籍,传颂千古的历史佳话。历来据此写成的演义式小说与戏曲传奇不胜枚举。人们饱蘸浓墨,将伍子胥塑造成一个忠肝义胆、忍耻雪恨、鞭挞昏君的大侠,通过这个鲜明的典型形象和故事宣泄出对统治者的强烈的反抗精神。至于历史上是否确有“掘墓鞭尸”这一幕,迄今为止却并没有任何人明确提出过疑义。当代学者张君认为,只要对诸史细加考辨即可发现,这件事原系子虚乌有。他的论据如下:
一、按《春秋》笔法与义例,凡有乱臣贼子以下凌上之事发生,莫不口诛而笔伐。孟子曾曰,“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滕文公下》)。按此,则楚平王虽听谗信诬,杀戮忠良,是一个典型的昏君暴主,但倘若伍子胥掘其墓,鞭其尸,仍会被《春秋》视为非分之道,大书特书,贬其为犯上作乱的叛臣贼子。可是《春秋》定公四年对吴兵入郢这件事的记载却极其简赅,仅仅只有五个字:“庚辰,吴入郢。”如此淡淡一笔便透露出定公四年并没有发生“掘墓鞭尸”这件僭冒至极的“暴行”。
二、《左传》记楚事尤为详备,宋代郑樵甚至因此断言:“左氏之书序楚事最详,则左氏为楚人。”但《左传》定公四年记吴兵入郢后的文字只寥寥数笔:“庚辰,吴入郢,以班处宫。子山处令尹之宫,夫概王欲攻之,惧而去之,夫概王入之。”据此可见,吴兵入郢后,吴国的第二号人物夫概王(阖庐弟)与第三号人物(阖庐子)之间便因争占楚国宫室,把偌大的一个郢城闹得乌烟瘴气。当时,派出去追歼逃亡在途的楚国君臣的只是少许部队,遇到一个执意庇护昭王的小小随国,便奈何不得,扫兴而归。在这种情况下,吴兵又有何暇费工旷日去为子胥、伯盉二人钻穴锥埋、掘墓鞭尸呢?何况,如真有此事发生,那么按《左传》惯例,通常也会在传文后照应或补著一笔的。
三、不论是《国语》之《楚语》、《吴语》,还是先秦诸子,均没有一字一句提及掘墓鞭尸。《国语》作为国别史,较多地保持了列国史书记载的原貌和素材,没有给予过多的加工、熔铸。先秦诸子有的生活在吴楚大战当时,有的虽生活于战国中后期,但因相去不远而对这场大战记忆犹新。但他们中谁也不曾提起或言及这件事。如果不是就根本没有这回事,那么上述诸书保持缄默有意不载岂非咄咄怪事!而且,伍子胥如果真的曾经引狼入室、掘墓鞭尸、淫乱宫闱的话,那么,不论是当代楚人,抑或是后世楚人,无疑都会笔伐之、口诛之、同仇共忾声讨之。但是遍寻史籍却没有一句这样的记载。另值得注意的是,如子胥果真掘平王之基,这一举动本身就辱及先人,何以据文献记载楚人还继续纪念并称颂伍氏先人在楚国的功绩和事迹呢?又,屈赋所涉楚史上的悬疑怪异之事甚多,可是也未有只言片语说到“掘墓鞭尸”事,而尤令人诧异不已的是,屈原在《九章》中反而极其称颂并自拟于伍子胥。《涉江》云:“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惜往日》云:“吴信谗而弗昧兮,子胥死而后忧。”《悲回风》云:“浮江淮而入海兮,从子胥而自适。”楚人对伍子胥的倾心颂扬,雄辩地证明了伍子胥没有“掘墓鞭尸”!
传世经籍中最早记载这件事的是较诸子为晚的《吕氏春秋》。其《首时篇》曰:伍子胥“亲射入宫,鞭荆平之坟三百。”不过,这里说的还只是“鞭坟”,而不是“鞭尸”。文献中与此记载大致相同的是《春秋谷梁传》。但《谷梁传》与《吕氏春秋》成书的年代均晚于诸子和《左传》。桓谭《新论》认为《左传》较《公羊》、《谷梁》“为近得实”,《左传》传世后百有余年,《公羊》、《谷梁》方作。《公羊》定公四年也未言及伍子胥亲自参加入郢之战和“掘墓鞭尸”一事。此外,《公羊》载伍子胥曰:“诸侯不为匹夫兴师。且臣闻之,事君犹事父也,亏君之义,复父之仇,臣不为也。”又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推刃之道也。”伍子胥慨然在吴王面前表白了心迹,且这些心迹又确实合乎“春秋”通义,他怎么会话音未落便背信食言,乘入郢之机去鞭平王之墓呢?显然,在这一点上,把《公羊》阐发春秋道义与《吕氏春秋》所载“鞭墓”说糅合在一处的《谷梁》,难以自圆其说。
史籍中最早而又最明确地记载伍子胥“掘墓鞭尸”事的是《史记》。《伍子胥列传》云:“及吴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在本传后,司马迁还高度赞扬伍子胥道:“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不难看出,司马迁是极力渲染和塑造伍子胥隐耻雪恨的烈丈夫气概和大侠形象的始作俑者。司马迁为伍子胥单列一传,刻意描述了其壮烈的事迹,及至东汉,伍子胥进而成为我国最早的演义式小?说——?赵晔《吴越春秋》中重点塑造的艺术典型,而“掘墓鞭尸”的情节也被加工、夸张得更活灵活现了。如《吴越春秋》卷上《阖庐内传》载:“吴王入郢上留,伍胥以不得昭王,乃掘平王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左足践腹,右手抉其目,诮之曰:‘谁使汝用谗谀之口,杀我父兄?岂不冤哉/即令阖庐妻昭王夫人,伍胥、孙武、白喜亦妻子常、司马戌之妻,以辱楚之君臣也。”
与赵晔同为越籍人的袁康、吴君高所撰《越绝书》与《吴越春秋》在风格、体例上颇相类似,其书卷一云:“子胥救蔡而伐荆。十五战,十五胜,荆平王已死,子胥将卒六千,操鞭捶笞平王之墓而数之,曰‘昔者吾先人无罪而子杀之,今此报子也’。”虽然颇为渲染,但却只写到“鞭墓”为止。这反映出“掘墓鞭尸”说在两汉时期虽风靡遐迩,但并未被多数学者所接受,即或像袁康、吴君高这一类学者也采取的是将信将疑、审慎折衷的态度。
张君认为,“掘墓鞭尸”之所以造说于战国末际与两汉,与当时的时代氛围有很大的关系。战国、两汉是复仇之风炽盛的时代,凡读过《史?记·?游侠列传》及东汉马援《诫二侄书》,即可概见侠士的社会地位及影响是何等隆重而广大了,被塑造成大侠的“伍子胥”就正好投合了这种时尚。而后世学人又大多笃信“太史公书”,这便是“掘墓鞭尸”说传流至今的原因所在。伍子胥是否掘墓鞭尸,从历史记载中分析
根据《史记·列传》的记载,伍子胥曾与申包胥交好,他在逃离楚国时对包胥说:“我必覆楚。”而包胥回答:“我必存之。”后来,吴军攻入郢都,伍子胥寻找楚昭王,未能找到,于是掘开了楚平王的墓,取出其尸体,鞭打了三百下,才停止。申包胥逃至山中,派人告诉伍子胥说:“你报仇的行为,是否太过分了!我听说,人数众多者能胜过天,天意也能破坏人的计划。你本是平王的臣子,曾面对面地事奉他,现在却至于侮辱死去的君王,这难道不是违背天道的极点吗!”从这些记载来看,伍子胥鞭尸的行为是有事实依据的,但我们不能仅仅从一方面来看待这个问题。
伍子胥是否真的掘墓鞭尸呢?我们来分析一位学者的观点。
学者张君认为,只要仔细考辨各种史籍,就能发现“掘墓鞭尸”这件事实际上并不存在。他的论据包括:
一、按照《春秋》的笔法和义例,对于乱臣贼子等以下犯上的行为,通常会口诛笔伐。孟子曾言:“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惧,作《春秋》。”如果楚平王虽然昏庸,但伍子胥掘墓鞭尸,仍会被视为非分之道,而《春秋》定公四年对吴兵入郢的记载却极其简略,只说“庚辰,吴入郢。”没有提及掘墓鞭尸的事情。
二、《左传》对楚国事务的记载尤为详尽,但定公四年记吴兵入郢后的文字,只简单提到了吴国的一些将领争夺楚宫的事情,并没有提到掘墓鞭尸。如果真的有这件事发生,那么按照《左传》的习惯,通常会在传文后对应地补充一笔。
三、无论是《国语》的《楚语》、《吴语》,还是先秦诸子,都没有提及掘墓鞭尸的事情。《国语》作为国别史,较多地保持了列国史书的原文和素材,没有过多的加工和熔铸。先秦诸子有的生活在吴楚大战当时,有的虽生活于战国中后期,但因相去不远而对这场大战记忆犹新。但他们中谁也没有提起或言及这件事。如果不是根本没有这回事,那么上述诸书保持沉默不载,岂非怪事!而且,如果伍子胥真的曾经引狼入室、掘墓鞭尸、侮辱宫闱,那么,不论是当代楚人,抑或是后世楚人,无疑都会口诛笔伐之、同仇敌忾声讨之。但是遍寻史籍却没有一句这样的记载。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如子胥果真掘平王之基,这一举动本身就辱及先人,何以楚人还继续纪念并称颂伍氏先人在楚国的功绩和事迹呢?又,屈赋所涉楚史上的悬疑怪异之事甚多,可是也未有只言片语说到“掘墓鞭尸”事,而尤令人诧异不已的是,屈原在《九章》中反而极其称颂并自拟于伍子胥。
传世经籍中最早记载这件事的是《吕氏春秋》。其《首时篇》称伍子胥“亲射入宫,鞭荆平之坟三百。”不过,这里说的还只是“鞭坟”,而不是“鞭尸”。文献中与此记载大致相同的是《春秋谷梁传》。但《谷梁传》与《吕氏春秋》成书的年代均晚于诸子和《左传》。桓谭《新论》认为《左传》较《公羊》、《谷梁》“为近得实”,《左传》传世后百有余年,《公羊》、《谷梁》方作。《公羊》定公四年也未言及伍子胥亲自参加入郢之战和“掘墓鞭尸”一事。此外,《公羊》载伍子胥曰:“诸侯不为匹夫兴师。且臣闻之,事君犹事父也,亏君之义,复父之仇,臣不为也。”又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推刃之道也。”伍子胥激昂地表白了心迹,且这些心迹又确实合乎“春秋”通义,他怎么会话音未落便背信食言,乘入郢之机去鞭平王之墓呢?显然,在这一点上,把《公羊》阐发春秋道义与《吕氏春秋》所载“鞭墓”说糅合在一处的《谷梁》,难以自圆其说。
史籍中最早而又最明确地记载伍子胥“掘墓鞭尸”事的是《史记》。《伍子胥列传》称:“及吴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在本传后,司马迁还高度赞扬伍子胥道:“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不难看出,司马迁是极力渲染和塑造伍子胥隐耻雪恨的烈丈夫气概和大侠形象的始作俑者。司马迁为伍子胥单列一传,刻意描述了其壮烈的事迹,及至东汉,伍子胥进而成为我国最早的演义式小?说——?赵晔《吴越春秋》中重点塑造的艺术典型,而“掘墓鞭尸”的情节也被加工、夸张得更活灵活现了。如《吴越春秋》卷上《阖庐内传》载:“吴王入郢上留,伍胥以不得昭王,乃掘平王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左足践腹,右手抉其目,诮之曰:‘谁使汝用谗谀之口,杀我父兄?岂不冤哉/即令阖庐妻昭王夫人,伍胥、、白喜亦妻子常、司马戌之妻,以辱楚之君臣也。”
与赵晔同为越籍人的袁康、吴君高所撰《越绝书》与《吴越春秋》在风格、体例上颇相类似,其书卷一云:“子胥救蔡而伐荆。十五战,十五胜,荆平王已死,子胥将卒六千,操鞭捶笞平王之墓而数之,曰‘昔者吾先人无罪而子杀之,今此报子也’。”虽然颇为渲染,但却只写到“鞭墓”为止。这反映出“掘墓鞭尸”说在两汉时期虽风靡遐迩,但并未被多数学者所接受,即或像袁康、吴君高这一类学者也采取的是将信将疑、审慎折衷的态度。
张君认为,“掘墓鞭尸”之所以造说于战国末际与两汉,与当时的时代氛围有很大的关系。战国、两汉是复仇之风炽盛的时代,凡读过《史?记·?游侠列传》及东汉马援《诫二侄书》,即可概见侠士的社会地位及影响是何等隆重而广大了,被塑造成大侠的“伍子胥”就正好投合了这种时尚。而后世学人又大多笃信“太史公书”,这便是“掘墓鞭尸”说传流至今的原因所在。